close
對話導演鵬飛:《米花之味》不僅是留守兒童和返鄉母親的故事
《米花之味》劇照。台中申請商標代辦
采訪鵬飛導演非常放松,他熟練地卷著煙,同時和記者聊《米花之味》。2015年,這位青年導演執導的北漂題材電影《地下香》獲得第7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威尼斯日單元”的最佳影片,今年,他的第二部長片《米花之味》再次入圍今年第74屆“威尼斯日“單元。申請註冊商標台中
《米花之味》講述瞭英澤飾演的單身媽媽從城市回到傢鄉展開新生活的故事。常年在外工作讓她與傢鄉人之間在生活方式與思考方式上產生瞭一些不同,他們需要以新的方式重新融入彼此的生活。而在融入女兒生活的過程中,修補關系的過程卻不是那麼順利。有一天,女兒和小夥伴因為偷走寨子裡最神聖的寺廟裡供奉的錢花被抓起來,村民們認為女孩們被“惡魔附身”。為瞭“拯救”她們,村民們決定潑水節期間,去祭拜一尊藏在具有1.2億年歷史溶洞中的石佛。
開始拍攝前,鵬飛在雲南體驗瞭一年生活,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在留守兒童/回鄉青年題材的故事中註入自己的思考,描繪瞭很多直指現實的問題:生存與傢庭、農村與城市、求神與回音、新與舊、中與西、男與女的碰撞等等。同時將飽滿的顏色與鮮活的生命力捕捉在鏡頭中。
作為攝影指導的廖本榕已經年近70,但幾乎每件事都親自上陣,在高低起伏的地勢上奔走著看景、拍攝、換鏡位;鵬飛還邀請到瞭北野武《座頭市》的配樂大師鈴木慶一,將自己的風格與當地樂器碰撞出瞭耳目一新的靈氣;女主角英澤也是體驗生活4個月,與世隔絕般地融入山村少數民族生活。《米花之味》將於意大利時間9月7日在威尼斯電影節與觀眾們見面。在這之前,記者在威尼斯電影節邀請到鵬飛導演就該片接受采訪,也瞭解到瞭一位青年導演對創作、對世界的思考。
對話鵬飛
Q:希望能聽您聊一下您自己的經歷以及拍攝《米花之味》的背景。
A:我19歲高中畢業去法國上學,先學兩年學法語,然後就進入瞭電影學院,學校要求每年放假都得實習並記分數,畢業實習尤為重要。找畢業實習很難,我記得我每天透過公寓的小窗望著天,等待著實習的消息,半年後,我接到一個電話,說是華語導演要在巴黎拍戲,需要人手,我就去瞭,原來是蔡明亮導演在巴黎拍《臉》(2009)。從那以後我就開始跟蔡導工作學習,我覺得自己很幸運。2014年拍瞭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地下香》,講的是住在地下室的北漂的故事。《米花之味》是在講城市飽和之後返鄉青年的故事,這其實也是我在拍完《地下香》之後就在構思的內容,正好社工聯合會有拍一部關於“留守兒童”影片的計劃,在他們的協助下我來到瞭中緬邊境一個傣族寨子,現在回想一下,一切都是緣分。
《地下香》海報。
Q:選擇這個地點是因為比較貼近中國鄉村嗎?
A:當時我還不知道去哪個地方展開工作,有一次社工在北京開年會,他們評選中國十大社工,其中一位正是負責留守兒童這一塊,她是雲南大學的社會學老師。後來我就聯系上她,她說雲南有三個地方他們的工作做的不錯,其中一個地方叫滄源,在中國邊境,距離緬甸15分鐘車程,可以去那裡看看。沒想到這一看,就是一年。我跟他們一起過潑水節、閉門節、開門節,還參加婚禮,搬新房什麼的。跟社工一起走傢串巷,慢慢積累著這些故事。我一開始沒有跟他們說我要在這裡拍電影,因為我希望他們能展現出真實的一面給我。很快我跟這裡的年輕人成為瞭朋友,他們對我都很好,今天去這傢吃飯明天去那傢吃飯,給我講瞭很多這裡的故事,當然,很多老人都認為我是人販子,時刻提醒著他們的孩子離我遠點,這種懷疑持續瞭半年多。
《米花之味》劇照。
在《米花之味》中飾演女主角的英澤。
Q:聽您說英澤為瞭演好女主角,花瞭很多精力和時間學習方言,還把自己曬黑瞭不少。
A:這是我第二次和英澤合作,通過“地下香”的拍攝,我發現她是一個很有毅力的演員,也很有靈氣,領悟力非常強。其實生活中據我瞭解,她也是很有毅力的一個人。她是在開拍前4個月到達滄源。為瞭塑造好一個傣族女子的形象,她和當地的女子們成為好友,加入她們的生活,然後和她們一樣忙碌起來,早上一起賣早點,賣米線,中午回到寨子裡劈柴做飯,然後喂豬洗衣服曬谷子等等,晚上還要排練舞蹈,並且要和小演員增進感情,兩“母女”在寨子周圍“遊山玩水”,似乎比我的籌備工作還忙,想約她試妝都難敲時間。在拍攝中我們也有很好的默契,稍微調整一下她就知道我要什麼。我喜歡她塑造的堅強內斂有韌性的女性形象,在男權社會中,堅強的女性也許不那麼受青睞,但我認為其實很多女性比男性更堅韌。
在《米花之味》中飾演女主角的英澤。
拍攝工作照。
Q:我看的時候覺得很多畫面的構圖很精致,顏色飽和度也很高。這些會給您取景、拍攝帶來難度嗎?
A: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請到廖本榕老師。他從《青少年哪吒》開始一直到《郊遊》都擔任蔡導的攝影指導(除瞭《你那邊幾點》)。我非常喜歡他的構圖美學,非常有張力,大氣。他機器擺下去,人在裡邊走動,我就覺得有濃濃的電影感。
關於《米花之味》的影像風格。廖先生是開機前兩個星期來到滄源,感受這裡的顏色、空氣稀薄度等等,他心裡有個底瞭,然後我們開始討論分鏡頭劇本,回到比較老一點的創作方式:寫下很詳細的分鏡頭劇本,找美術組的同事幫我畫一畫比較難的戲的分鏡,等我們倆溝通好分鏡瞭,然後發給大傢。
我覺得他也是以一個老師的身份來教我,在分鏡頭上的把握與判斷,提高一個年輕導演腦中的鏡頭感,就好像在我的眼前裝瞭一個無形的鏡頭,來看自己的故事。我們努力把前期的工作做到最好,雖然到現場分鏡頭劇本基本都會被推翻,但是至少我們心裡有底,敢於在現場大膽改戲。而且我們兩個也比較有默契,我和廖先生關系很好,算是忘年交,我什麼都可以跟他說。比如我說,我真的沒有感覺,不知道怎麼說;或者是我想不出來,甚至我覺得您這個鏡頭可能擺的不好,等等,廖先生也不會介意,隻是“呲楞”一下站起來,去尋找其他機位瞭。
鵬飛與廖先生尋找機位。
Q:您還挺嚴苛的是嗎?
A:是的。即使說瞭一些不好意思的話,廖先生也不會怎麼樣。雖然他是資深的攝影師,臺灣電影幕後的元老級人物。他非常願意跟我溝通,瞭解一個新導演的想法。所以現在看到的鏡頭都是我們兩個精心討論過的。廖先生一直在幫我把想法呈現。
因為蔡導的電影是比較慢一點,每一個鏡頭就要紮實,要經得住觀看。但我的電影故事性會強一些,鏡頭不會那麼長。我和廖先生選擇的構圖方式就不會是每一個構圖都營造張力,因為這樣很多場戲下來會疲憊。所以有一個主體的概念支撐每場戲。然後我會再抓人物的一些細節,我很願意再動一動,用運鏡來找一些比較好玩的事兒。比如母女搶手機那場戲,兩個人在鬥智鬥勇,但是又很調皮。這個時候廖先生就說要推軌,要動起來。可能之前廖先生給大傢的印象是“固定機位”,但其實他有很多主意,隻不過他是很願意去琢磨導演的想法,幫導演實現他腦海裡的影像。
《米花之味》劇照。
拍攝工作照。
Q:您能繼續講一下音樂方面的特色嗎?
A:我很喜歡北野武電影中的幹凈、簡單,但是該有爆發力的時候也不含糊,而且有一種很好的節奏或者幽默感在裡面,包括他的音樂也很棒。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就在想我怎麼去做好音樂這部分。如何既有少數民族風情又有現代音樂的元素,如何用當地的樂器又不拘泥於傳統,後來我就想起北野武的《座頭市》,裡面的音樂就是用瞭很多鋤頭鋤地的聲音,或者是腳步聲,或者是木屐發出的聲音組成。然後我就一直聽《座頭市》的原聲,並決定找鈴木慶一先生幫我作曲。過瞭一段日子收到他的回信,他說他很喜歡劇本,願意加入,我很高興。他也很敬業,第一次來中國就來到雲南,他說需要感受這裡的氣味、顏色甚至這裡的空氣濕度,這些東西對他的創作都是非常有用的。來瞭之後就呆在傣族寨子裡靜靜地看著我們拍戲。
《米花之味》劇照。
我們那個地方不好走,從昆明開車要兩天才到。他們是轉機到臨滄市的機場,再開五個多小時山路到我們這個地方。我聯系到瞭當地文工團的一個人,把所有傣族樂器一一演奏給鈴木聽,鈴木就把音節一個一個地錄下來。到(拍攝)現場寺廟裡的象腳鼓,還有傣族的鋩,還有雲南敲叮叮糖(麥芽糖)的聲音,他也去收錄。還有像滴水似的鼓聲,那些樂器是從印度那邊傳過來。
起初,我告訴他我想用傳統音樂的調性,他做瞭一個版本,結果太傳統瞭,太民族瞭。 我想我不要遏制住作曲傢的想法,就告訴他按照他的感覺來創作試試看。他也知道劇本,也看瞭大概的狀況和風格,之後他一做出來就基本是現在大傢聽到的這樣,我覺得很棒,是我在找的感覺。
《米花之味》劇照。
Q:我也覺得帶來瞭不一樣的感覺,甚至與電影達到瞭復調的合聲效果。關於影片主題我有一個問題,您會不會您在片中想講的東西比較多,最後的關於留守兒童或是回鄉青年的主題沒有被突出?
A:你看的時候有覺得不突出嗎?
Q:可能我看的時候知道是在講兒童,一開始我沒有覺得那麼明顯,後來小女孩的朋友生病之後,感覺比較明確的知道您要講什麼。所以您也有質疑自己嗎?
A:我沒有質疑過自己,而且我覺得這正是最有魅力的地方。它不光是講留守兒童或返鄉母親的故事,還有在講圍繞在她們周圍的事情,她們生活的環境,甚至是對一些更深入的問題進行討論。
比如溶洞這場戲。 進入溶洞後,希望大傢忘掉之前的故事。溶洞是另外一個世界,以母女為代表的人類,面對大自然是如此渺小,圍繞在她們周圍的故事更是歷史的一瞬,那麼我們在做著什麼?什麼是人類得以存活的最寶貴的東西?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情感。我想退遠一點來看這兩個人,和她們面臨的問題,或者看整個人類面臨的問題。
《米花之味》劇照。
Q:您是說留守兒童隻是一個話題,其實您要講的是根植在這個話題下面的東西?
A:是的,我是要把它升華一下,可能你說留守兒童為什麼會出現,是經濟發展不平均,因為大傢去外地打工賺更多錢,再大一點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眾多故事。但這些問題一放到大自然中,就是一瞬間的事情。反過來想,在這個溶洞裡,這一刻,隻有這一對人類母女。可以說他們是為佛跳舞,也是為彼此祝福,也是為瞭死去的孩子超渡,也是為瞭祈福寨子不要再有更多(不好)的事情。這樣說可能比較誇張,這對母女對我來講是為人類跳舞。我希望能跳出來看人類現在在做什麼,我們到底是從哪來,要如何去哪裡,什麼對我們最根本,最重要。
Q:當地的佛教會不會比較世俗化?是有求於佛才來拜佛的?
A:他們還是很虔誠的。每一個寨子都有個寺廟,寺廟的規模大小要看寨子經濟實力,每一傢老人都輪流供養寺廟中的長老。每天都要念經,是很虔誠的,並不是有求於佛才做這些事情。每個節日都和宗教有關。
Q:他們求助於那個類似於神婆的角色,她說“看不見的白馬”是有什麼寓意嗎?
A:沒有刻意設立寓意,這是寨子裡的人跟我講的一個事情。當地人會信山神的存在,他們在田裡幹瞭什麼神都知道,比如過分開墾,砍伐樹這些山神都知道。我基本上隻把山神說的話照搬過來用作臺詞,山神“附身的”神婆真是在教育他們不要去打野生動物。據說有一次他們打獵的時候經常被蛇咬,就去求助山神,她說你們不再去打那些野生動物,蛇就不會再來咬你們。後來他們沒打瞭,再去砍柴就沒事瞭。我也是聽說的,當地每個人都篤信不疑,你可以認為它是迷信,也可以認為是當地的一個習俗,總之我覺得還挺美的。
Q:小女孩發燒的時候,傢裡人沒有帶她去第一時間去醫院,但是第一時間請瞭一個“叫魂”的人是嗎。那您是怎麼看這種情況的?
A:“叫魂”是當地的一個習俗,遠方歸來或者是要出遠門或者生病,都是要“叫魂”的。電影中的情節是在講當地的一個風俗,講隔代教育的弊端、留守兒童面臨的處境等等。
《米花之味》劇照。
Q:最終的成品您是滿意的嗎?
A:我還是很滿意的。我在慢慢尋找自己的風格,目前這個風格雛形我覺得是對的。
Q:您是怎麼做到的形成自己獨立的風格的,片中基本上沒有看到太多的蔡導風格烙印?
A:我想找自己的東西。我跟著蔡導拍戲大概有四五年,包括做副導演與編劇等工作。《地下香》的劇本,蔡導也幫我看過,提出很多重要的意見。當你掉進蔡導的美學中很難抽出來,我拍《地下香》的時候我,怎麼擺都覺得不好看,隻有擺成蔡導那樣的構圖才好看。我說完蛋瞭,這樣不行,因為世界上隻有一個蔡明亮。我要試圖找到自己的感覺,我把自己想象成觀眾,在想是什麼樣的電影,可能讓我更喜歡看,更符合我的性格,是我感興趣的。就像剛才討論溶洞的話題,是我感興趣的一個領域。我之後寫劇本都會試圖抽離出來看,慢慢地找到自己。
我也很願意吸收蔡導很棒的地方,比如說劇作方面,或者,他非常擅長用鏡頭來說話,用演員的走位、演員的狀態來說話。就算演員坐那抽根煙,你都覺得他有戲。我也願意去學習他,但他這些東西很復雜,很難學到,我隻能盡量去接近他好的東西。
《米花之味》劇照。
Q:所以本片還是基於您比較私人化的審美、體驗和個性進行一個探索吧。
A:是的,比如說試映的時候有位觀眾問到為什麼(面部特寫時)情感表達比較少,我是覺得生活中通常沒有那麼多表情,所以電影中我也不想有太多的表情,而是以他們的行動,或者說面對問題做出的反映,或者人物在不同處境中的狀態來表現內心。比如說媽媽開車獨處時候,或者是剛回來和孩子還不太熟悉的時候,就是沒有太多表情的吧,可能我覺得有一些人沒有太多表情的時候,其實心裡卻是翻來覆去。我很喜歡這樣的表達,比如北野武,他也沒有多少表情,但是內心情緒很多。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場景是在“大佬”裡面,他跟他的馬仔去和另一個社團談合作,最後沒談下來,他們剛要坐車離開。結果大馬仔(寺島進飾)就沒上車,給北野武鞠瞭一躬,說他還有事,目送車走後,他回去繼續和那邊談合作,最終以自殺的方式表達瞭誠意,促成瞭合作。然後剪接到北野武這邊,他沒有表情,戴一墨鏡也看不到他眼睛。但是這種兄弟之間的感情一下就出來瞭。北野武知道他的兄弟在做什麼,心裡也會記住,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見面。我覺得這個勝過直接讓演員說“我很痛苦,我很糾結”這類比較外露的情感表達。
特朗普上任兩周簽8條行政命令
號外號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強,買不瞭吃虧,買不瞭上當,是XX你就堅持60秒!
台灣商標註冊查詢
《米花之味》劇照。台中申請商標代辦
采訪鵬飛導演非常放松,他熟練地卷著煙,同時和記者聊《米花之味》。2015年,這位青年導演執導的北漂題材電影《地下香》獲得第7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威尼斯日單元”的最佳影片,今年,他的第二部長片《米花之味》再次入圍今年第74屆“威尼斯日“單元。申請註冊商標台中
《米花之味》講述瞭英澤飾演的單身媽媽從城市回到傢鄉展開新生活的故事。常年在外工作讓她與傢鄉人之間在生活方式與思考方式上產生瞭一些不同,他們需要以新的方式重新融入彼此的生活。而在融入女兒生活的過程中,修補關系的過程卻不是那麼順利。有一天,女兒和小夥伴因為偷走寨子裡最神聖的寺廟裡供奉的錢花被抓起來,村民們認為女孩們被“惡魔附身”。為瞭“拯救”她們,村民們決定潑水節期間,去祭拜一尊藏在具有1.2億年歷史溶洞中的石佛。
開始拍攝前,鵬飛在雲南體驗瞭一年生活,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在留守兒童/回鄉青年題材的故事中註入自己的思考,描繪瞭很多直指現實的問題:生存與傢庭、農村與城市、求神與回音、新與舊、中與西、男與女的碰撞等等。同時將飽滿的顏色與鮮活的生命力捕捉在鏡頭中。
作為攝影指導的廖本榕已經年近70,但幾乎每件事都親自上陣,在高低起伏的地勢上奔走著看景、拍攝、換鏡位;鵬飛還邀請到瞭北野武《座頭市》的配樂大師鈴木慶一,將自己的風格與當地樂器碰撞出瞭耳目一新的靈氣;女主角英澤也是體驗生活4個月,與世隔絕般地融入山村少數民族生活。《米花之味》將於意大利時間9月7日在威尼斯電影節與觀眾們見面。在這之前,記者在威尼斯電影節邀請到鵬飛導演就該片接受采訪,也瞭解到瞭一位青年導演對創作、對世界的思考。
對話鵬飛
Q:希望能聽您聊一下您自己的經歷以及拍攝《米花之味》的背景。
A:我19歲高中畢業去法國上學,先學兩年學法語,然後就進入瞭電影學院,學校要求每年放假都得實習並記分數,畢業實習尤為重要。找畢業實習很難,我記得我每天透過公寓的小窗望著天,等待著實習的消息,半年後,我接到一個電話,說是華語導演要在巴黎拍戲,需要人手,我就去瞭,原來是蔡明亮導演在巴黎拍《臉》(2009)。從那以後我就開始跟蔡導工作學習,我覺得自己很幸運。2014年拍瞭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地下香》,講的是住在地下室的北漂的故事。《米花之味》是在講城市飽和之後返鄉青年的故事,這其實也是我在拍完《地下香》之後就在構思的內容,正好社工聯合會有拍一部關於“留守兒童”影片的計劃,在他們的協助下我來到瞭中緬邊境一個傣族寨子,現在回想一下,一切都是緣分。
《地下香》海報。
Q:選擇這個地點是因為比較貼近中國鄉村嗎?
A:當時我還不知道去哪個地方展開工作,有一次社工在北京開年會,他們評選中國十大社工,其中一位正是負責留守兒童這一塊,她是雲南大學的社會學老師。後來我就聯系上她,她說雲南有三個地方他們的工作做的不錯,其中一個地方叫滄源,在中國邊境,距離緬甸15分鐘車程,可以去那裡看看。沒想到這一看,就是一年。我跟他們一起過潑水節、閉門節、開門節,還參加婚禮,搬新房什麼的。跟社工一起走傢串巷,慢慢積累著這些故事。我一開始沒有跟他們說我要在這裡拍電影,因為我希望他們能展現出真實的一面給我。很快我跟這裡的年輕人成為瞭朋友,他們對我都很好,今天去這傢吃飯明天去那傢吃飯,給我講瞭很多這裡的故事,當然,很多老人都認為我是人販子,時刻提醒著他們的孩子離我遠點,這種懷疑持續瞭半年多。
《米花之味》劇照。
在《米花之味》中飾演女主角的英澤。
Q:聽您說英澤為瞭演好女主角,花瞭很多精力和時間學習方言,還把自己曬黑瞭不少。
A:這是我第二次和英澤合作,通過“地下香”的拍攝,我發現她是一個很有毅力的演員,也很有靈氣,領悟力非常強。其實生活中據我瞭解,她也是很有毅力的一個人。她是在開拍前4個月到達滄源。為瞭塑造好一個傣族女子的形象,她和當地的女子們成為好友,加入她們的生活,然後和她們一樣忙碌起來,早上一起賣早點,賣米線,中午回到寨子裡劈柴做飯,然後喂豬洗衣服曬谷子等等,晚上還要排練舞蹈,並且要和小演員增進感情,兩“母女”在寨子周圍“遊山玩水”,似乎比我的籌備工作還忙,想約她試妝都難敲時間。在拍攝中我們也有很好的默契,稍微調整一下她就知道我要什麼。我喜歡她塑造的堅強內斂有韌性的女性形象,在男權社會中,堅強的女性也許不那麼受青睞,但我認為其實很多女性比男性更堅韌。
在《米花之味》中飾演女主角的英澤。
拍攝工作照。
Q:我看的時候覺得很多畫面的構圖很精致,顏色飽和度也很高。這些會給您取景、拍攝帶來難度嗎?
A: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請到廖本榕老師。他從《青少年哪吒》開始一直到《郊遊》都擔任蔡導的攝影指導(除瞭《你那邊幾點》)。我非常喜歡他的構圖美學,非常有張力,大氣。他機器擺下去,人在裡邊走動,我就覺得有濃濃的電影感。
關於《米花之味》的影像風格。廖先生是開機前兩個星期來到滄源,感受這裡的顏色、空氣稀薄度等等,他心裡有個底瞭,然後我們開始討論分鏡頭劇本,回到比較老一點的創作方式:寫下很詳細的分鏡頭劇本,找美術組的同事幫我畫一畫比較難的戲的分鏡,等我們倆溝通好分鏡瞭,然後發給大傢。
我覺得他也是以一個老師的身份來教我,在分鏡頭上的把握與判斷,提高一個年輕導演腦中的鏡頭感,就好像在我的眼前裝瞭一個無形的鏡頭,來看自己的故事。我們努力把前期的工作做到最好,雖然到現場分鏡頭劇本基本都會被推翻,但是至少我們心裡有底,敢於在現場大膽改戲。而且我們兩個也比較有默契,我和廖先生關系很好,算是忘年交,我什麼都可以跟他說。比如我說,我真的沒有感覺,不知道怎麼說;或者是我想不出來,甚至我覺得您這個鏡頭可能擺的不好,等等,廖先生也不會介意,隻是“呲楞”一下站起來,去尋找其他機位瞭。
鵬飛與廖先生尋找機位。
Q:您還挺嚴苛的是嗎?
A:是的。即使說瞭一些不好意思的話,廖先生也不會怎麼樣。雖然他是資深的攝影師,臺灣電影幕後的元老級人物。他非常願意跟我溝通,瞭解一個新導演的想法。所以現在看到的鏡頭都是我們兩個精心討論過的。廖先生一直在幫我把想法呈現。
因為蔡導的電影是比較慢一點,每一個鏡頭就要紮實,要經得住觀看。但我的電影故事性會強一些,鏡頭不會那麼長。我和廖先生選擇的構圖方式就不會是每一個構圖都營造張力,因為這樣很多場戲下來會疲憊。所以有一個主體的概念支撐每場戲。然後我會再抓人物的一些細節,我很願意再動一動,用運鏡來找一些比較好玩的事兒。比如母女搶手機那場戲,兩個人在鬥智鬥勇,但是又很調皮。這個時候廖先生就說要推軌,要動起來。可能之前廖先生給大傢的印象是“固定機位”,但其實他有很多主意,隻不過他是很願意去琢磨導演的想法,幫導演實現他腦海裡的影像。
《米花之味》劇照。
拍攝工作照。
Q:您能繼續講一下音樂方面的特色嗎?
A:我很喜歡北野武電影中的幹凈、簡單,但是該有爆發力的時候也不含糊,而且有一種很好的節奏或者幽默感在裡面,包括他的音樂也很棒。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就在想我怎麼去做好音樂這部分。如何既有少數民族風情又有現代音樂的元素,如何用當地的樂器又不拘泥於傳統,後來我就想起北野武的《座頭市》,裡面的音樂就是用瞭很多鋤頭鋤地的聲音,或者是腳步聲,或者是木屐發出的聲音組成。然後我就一直聽《座頭市》的原聲,並決定找鈴木慶一先生幫我作曲。過瞭一段日子收到他的回信,他說他很喜歡劇本,願意加入,我很高興。他也很敬業,第一次來中國就來到雲南,他說需要感受這裡的氣味、顏色甚至這裡的空氣濕度,這些東西對他的創作都是非常有用的。來瞭之後就呆在傣族寨子裡靜靜地看著我們拍戲。
《米花之味》劇照。
我們那個地方不好走,從昆明開車要兩天才到。他們是轉機到臨滄市的機場,再開五個多小時山路到我們這個地方。我聯系到瞭當地文工團的一個人,把所有傣族樂器一一演奏給鈴木聽,鈴木就把音節一個一個地錄下來。到(拍攝)現場寺廟裡的象腳鼓,還有傣族的鋩,還有雲南敲叮叮糖(麥芽糖)的聲音,他也去收錄。還有像滴水似的鼓聲,那些樂器是從印度那邊傳過來。
起初,我告訴他我想用傳統音樂的調性,他做瞭一個版本,結果太傳統瞭,太民族瞭。 我想我不要遏制住作曲傢的想法,就告訴他按照他的感覺來創作試試看。他也知道劇本,也看瞭大概的狀況和風格,之後他一做出來就基本是現在大傢聽到的這樣,我覺得很棒,是我在找的感覺。
《米花之味》劇照。
Q:我也覺得帶來瞭不一樣的感覺,甚至與電影達到瞭復調的合聲效果。關於影片主題我有一個問題,您會不會您在片中想講的東西比較多,最後的關於留守兒童或是回鄉青年的主題沒有被突出?
A:你看的時候有覺得不突出嗎?
Q:可能我看的時候知道是在講兒童,一開始我沒有覺得那麼明顯,後來小女孩的朋友生病之後,感覺比較明確的知道您要講什麼。所以您也有質疑自己嗎?
A:我沒有質疑過自己,而且我覺得這正是最有魅力的地方。它不光是講留守兒童或返鄉母親的故事,還有在講圍繞在她們周圍的事情,她們生活的環境,甚至是對一些更深入的問題進行討論。
比如溶洞這場戲。 進入溶洞後,希望大傢忘掉之前的故事。溶洞是另外一個世界,以母女為代表的人類,面對大自然是如此渺小,圍繞在她們周圍的故事更是歷史的一瞬,那麼我們在做著什麼?什麼是人類得以存活的最寶貴的東西?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情感。我想退遠一點來看這兩個人,和她們面臨的問題,或者看整個人類面臨的問題。
《米花之味》劇照。
Q:您是說留守兒童隻是一個話題,其實您要講的是根植在這個話題下面的東西?
A:是的,我是要把它升華一下,可能你說留守兒童為什麼會出現,是經濟發展不平均,因為大傢去外地打工賺更多錢,再大一點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眾多故事。但這些問題一放到大自然中,就是一瞬間的事情。反過來想,在這個溶洞裡,這一刻,隻有這一對人類母女。可以說他們是為佛跳舞,也是為彼此祝福,也是為瞭死去的孩子超渡,也是為瞭祈福寨子不要再有更多(不好)的事情。這樣說可能比較誇張,這對母女對我來講是為人類跳舞。我希望能跳出來看人類現在在做什麼,我們到底是從哪來,要如何去哪裡,什麼對我們最根本,最重要。
Q:當地的佛教會不會比較世俗化?是有求於佛才來拜佛的?
A:他們還是很虔誠的。每一個寨子都有個寺廟,寺廟的規模大小要看寨子經濟實力,每一傢老人都輪流供養寺廟中的長老。每天都要念經,是很虔誠的,並不是有求於佛才做這些事情。每個節日都和宗教有關。
Q:他們求助於那個類似於神婆的角色,她說“看不見的白馬”是有什麼寓意嗎?
A:沒有刻意設立寓意,這是寨子裡的人跟我講的一個事情。當地人會信山神的存在,他們在田裡幹瞭什麼神都知道,比如過分開墾,砍伐樹這些山神都知道。我基本上隻把山神說的話照搬過來用作臺詞,山神“附身的”神婆真是在教育他們不要去打野生動物。據說有一次他們打獵的時候經常被蛇咬,就去求助山神,她說你們不再去打那些野生動物,蛇就不會再來咬你們。後來他們沒打瞭,再去砍柴就沒事瞭。我也是聽說的,當地每個人都篤信不疑,你可以認為它是迷信,也可以認為是當地的一個習俗,總之我覺得還挺美的。
Q:小女孩發燒的時候,傢裡人沒有帶她去第一時間去醫院,但是第一時間請瞭一個“叫魂”的人是嗎。那您是怎麼看這種情況的?
A:“叫魂”是當地的一個習俗,遠方歸來或者是要出遠門或者生病,都是要“叫魂”的。電影中的情節是在講當地的一個風俗,講隔代教育的弊端、留守兒童面臨的處境等等。
《米花之味》劇照。
Q:最終的成品您是滿意的嗎?
A:我還是很滿意的。我在慢慢尋找自己的風格,目前這個風格雛形我覺得是對的。
Q:您是怎麼做到的形成自己獨立的風格的,片中基本上沒有看到太多的蔡導風格烙印?
A:我想找自己的東西。我跟著蔡導拍戲大概有四五年,包括做副導演與編劇等工作。《地下香》的劇本,蔡導也幫我看過,提出很多重要的意見。當你掉進蔡導的美學中很難抽出來,我拍《地下香》的時候我,怎麼擺都覺得不好看,隻有擺成蔡導那樣的構圖才好看。我說完蛋瞭,這樣不行,因為世界上隻有一個蔡明亮。我要試圖找到自己的感覺,我把自己想象成觀眾,在想是什麼樣的電影,可能讓我更喜歡看,更符合我的性格,是我感興趣的。就像剛才討論溶洞的話題,是我感興趣的一個領域。我之後寫劇本都會試圖抽離出來看,慢慢地找到自己。
我也很願意吸收蔡導很棒的地方,比如說劇作方面,或者,他非常擅長用鏡頭來說話,用演員的走位、演員的狀態來說話。就算演員坐那抽根煙,你都覺得他有戲。我也願意去學習他,但他這些東西很復雜,很難學到,我隻能盡量去接近他好的東西。
《米花之味》劇照。
Q:所以本片還是基於您比較私人化的審美、體驗和個性進行一個探索吧。
A:是的,比如說試映的時候有位觀眾問到為什麼(面部特寫時)情感表達比較少,我是覺得生活中通常沒有那麼多表情,所以電影中我也不想有太多的表情,而是以他們的行動,或者說面對問題做出的反映,或者人物在不同處境中的狀態來表現內心。比如說媽媽開車獨處時候,或者是剛回來和孩子還不太熟悉的時候,就是沒有太多表情的吧,可能我覺得有一些人沒有太多表情的時候,其實心裡卻是翻來覆去。我很喜歡這樣的表達,比如北野武,他也沒有多少表情,但是內心情緒很多。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場景是在“大佬”裡面,他跟他的馬仔去和另一個社團談合作,最後沒談下來,他們剛要坐車離開。結果大馬仔(寺島進飾)就沒上車,給北野武鞠瞭一躬,說他還有事,目送車走後,他回去繼續和那邊談合作,最終以自殺的方式表達瞭誠意,促成瞭合作。然後剪接到北野武這邊,他沒有表情,戴一墨鏡也看不到他眼睛。但是這種兄弟之間的感情一下就出來瞭。北野武知道他的兄弟在做什麼,心裡也會記住,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見面。我覺得這個勝過直接讓演員說“我很痛苦,我很糾結”這類比較外露的情感表達。
特朗普上任兩周簽8條行政命令
號外號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強,買不瞭吃虧,買不瞭上當,是XX你就堅持60秒!
台灣商標註冊查詢
AUGI SPORTS|重機車靴|重機車靴推薦|重機專用車靴|重機防摔鞋|重機防摔鞋推薦|重機防摔鞋
AUGI SPORTS|augisports|racing boots|urban boots|motorcycle boots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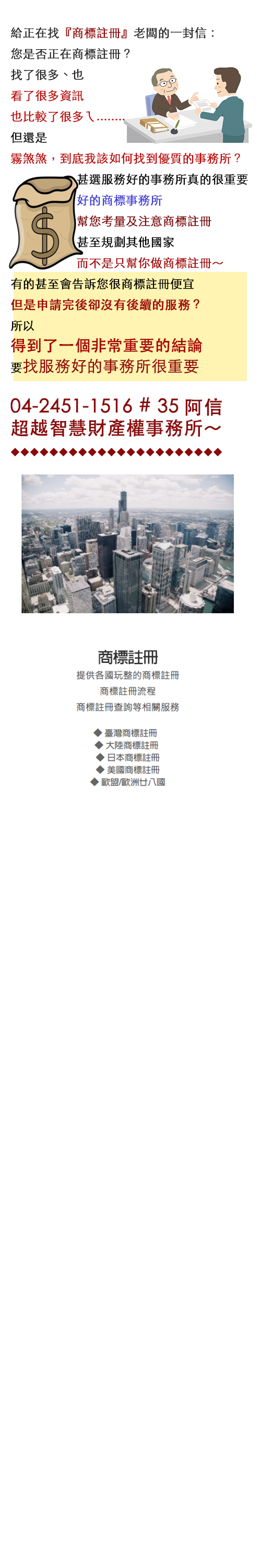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